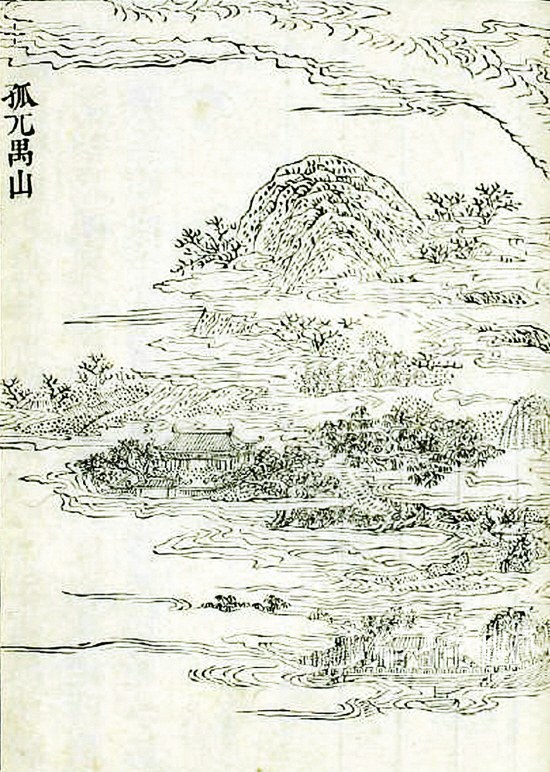天理难容 九、太委屈
luyued 发布于 2011-01-09 18:26 浏览 N 次
九、太委屈
樱仫才刚走,俊彦又进来了,看了众人那副表情,不解问:“谈得怎么样了?都不好吗?”
“嗯,还是再看看。”依美对上他那双疑惑的眼,无力地道:“一个爱赌,一个爱酒,一个爱上花楼,还有一个却长得不是一副人样,怎么选呀?!”
“有这么差劲吗?”他望着一脸沮丧的妹妹。
阿妹当下把樱仫刚才说的那番话照翻出来说了一遍。听得俊彦亦是无言以对。只是他心中明白,那几位公子是真有那么一点嗜好,也真或是有那么一点过火,可远不及樱仫说的夸张,他倒是挺能吹的!但樱仫已是先入为主,他倒也不便再说什么。
立夏这天,骆荟分娩了,是个儿子。
左京与健义欢喜得不得了,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口里怕化了,宝贝得让人妒忌。孩子是王旁辈的,取名胜玑。孩子满月后,府里方清静了些,可胜玑儿这些天不知是什么原因半夜总是哭啼,奶娘哄他不停,骆荟身子骨又没全好,急、气起来就骂,骂奶娘、骂奴婢,有进连那小儿子也骂进去。每每这时健义便温言相劝,骆荟抱怨几句就消下气来。
府中人人难以熟睡,不得安宁,介也无计可施,只得忍着。
最苦的要数尤尤雨烟。二女共伺一夫,同一房的人,自然住得比别人近些。两人的屋子就只隔着一个小庭院,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这边也知道。别说是夜深人静时了,就是大白天的,也好不烦燥。这些还都是外因素的刺激,那内心的煎熬就更折磨人了。
春梅很替主子不平,看她日渐消瘦,心中好不难过。
尤雨烟倚在窗前,静静地听着骆荟屋里的吵闹声。遥见院前一棵杏树下有一对男女在亲热,男子双手环住女子的腰,一会亲脸蛋一会亲脖项。尤雨烟虽已久为人妇,也不禁为他们的大胆而脸红。那女子躲开男子猛捶了他几下,继而两人又笑成一团,甚是甜蜜。
女子的一头秀发盘了起来,显是一名少妇……尤雨烟方认出原来是骆荟的丫头小丽和阿姚!两人婚前素无来往,婚后却发如胶似漆,她好生羡慕。想到自己与丈夫却是正好相反,温存早已没有,本来的相敬如宾更是因骆荟的加入而变得如陌路人一般。
尤雨烟偷偷拭去泪水,想避开院前的俩人,突觉头一重,倒了下来。
“奶奶,奶奶!?”春梅大惊,赶忙把她扶进屋里,又遣人去请大夫。
大夫只说她是身体虚弱,心力交瘁,要好生调养。开了张药方领了赏钱就去了。
春梅含泪侍候主子吃了药,一咬牙根迈出院子来到骆荟屋里。
小丽见了她,笑问:“真是稀客呀!春梅姐,什么风把你吹来了?”
春梅心中着急,不理会她的讽刺,左顾右盼道:“大爷在吗?”
小丽有点气,但想起丈夫阿姚让她凡事忍让些个,便没发作,一呶嘴道:“和奶奶在里面呢!”领着春梅进了内堂,在房门前停下:“爷,奶奶,春梅来了。”春梅在旁道:“爷,奶奶昏倒了,您快回去瞧瞧。”
骆荟一听,甚不欢喜,口中却道:“姐姐不舒服,请大夫了吗?要不要紧?”
“请大夫了,说是体虚,心力交瘁。”春梅答道:“奶奶一直昏迷着,奴婢心中又急又怕,只得来请爷。”
骆荟听她仍是左一句奶奶右一句请回,心中更怒。但见健义已露出担心的神色,也一脸着紧的样子:“既是如此,我也要去看看。”
健义道:“你刚坐完月子,身子也虚,就不必劳累了。我独自过去罢。”
“不,姐姐待我甚好,我怎样也放心不下。
“这……好吧。”
门外的小丽听了,忙推门进去侍候。骆荟起了床,双脚一着地,便倒在健义怀中,左手抱额,低声呻吟了一声。
健义忙抱住娇妻:“怎么了?”
“头……有点晕……不碍事。”她强装笑颜。
“你好好休息,下次再去罢。”健义扶她上床。
“不,我,我……”骆荟摇着头,但话刚出口却猛一阵咳,胀得满脸通红。
健义轻轻拍着她的背脊,又是着急,又是心痛。
“奶奶,您歇着点儿!”小丽忙倒了杯温茶递过去,“先喝口水顺顺气。”
骆荟终于咳停了,伸手接过杯子,一双手颤得利害,才举到半空“晃噹”一声杯子没拿稳,掉地上摔破了。她想说什么,却又是一阵咳嗽。
“奶奶!”小丽会过意来,转身对门外的春梅道:“我们奶奶的身子骨你也是知道的。你且先回去罢,一会儿爷自会过去。”
春梅咬着下唇,转身走了。
小丽一呶嘴,道:“走也不说一声,知道的还好,不知道的还道是尤奶奶不会教丫头呢!”
一旁的小荷道:“想来是春梅姐太着急尤奶奶了罢。”
小丽啐了一口:“着急起来便没了主子了,赶明儿我也急一急!”说完转身去侍候骆荟。
健义一直守着骆荟,只当没听到,而心中却有了计较:尤雨烟和春梅进门多年,不会连这点规矩也不知道,这春梅也太过份了些,在自己眼前尚且如此,不在眼前时呢?
尤雨烟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,听到声音便缓缓抬起脸来。春梅奔至床前,眼眶一红,竟说不出话来。尤雨烟心下明白,眼泪徐徐落下。主仆二人就这样样默默流泪。
一旁的小丫头夏儿看不过眼,劝道:“奶奶这也不是什么大病,慢慢调养自会好,可别哭坏了身子。”又对春梅道:“春梅姐姐,你不劝奶奶也就罢了,怎么自己先哭了起来?”
春梅忙收声不哭,倒了杯清茶给尤雨烟:“妹妹说的是,奶奶您也甭难过了,先呷口茶罢。”
夏儿扶起主子,两人侍候她喝了两口,便又躺下。春梅遣退夏儿,独自伴在尤雨烟床边。她不时悄悄往门口望去,却迟迟不见健义出现,背对着尤雨烟偷偷抹眼泪。
半夜里尤雨烟从梦中醒来,惊唤:“春梅,春梅!”
“奶奶,春梅在。”春梅哑声答应。
尤雨烟静了一阵子,道:“我想喝水。”
“我这就给您倒去。”春梅起身倒了半碗茶,喂她喝了。尤雨烟润了润嗓子,就摇摇头。春梅把剩下的小半碗吃了,又回到床边。
尤雨烟突然低问:“春梅,你怎么了?”
“没……”春梅嗓子一扁,又落下泪来。
“我的身子自己知道。”尤雨烟缓声道:“你不必太担心。”
“奶奶,大爷……”
尤雨烟鼻子一酸,仍轻道:“荟妹妹刚坐完月子,身子亦多有不适,你大爷在那边陪着她,也是应该的。”
春梅一哽,呜呜哭起来。
“傻丫头。”尤雨烟想说些安慰的话,无奈自己也滴下眼泪。
“我,刚才去骆奶奶那请大爷,大爷……大爷说要过来的!”
尤雨烟摇摇头,紧闭双目任由泪水滑下,只听春梅哽咽道:“奶奶的身子骨不好,是众所周知的。可自从骆奶奶进门后,他几曾来过这里?他刚说要来的!……人来来也不叫小林捎个信儿问候两句!那边屋里的竟是装作关心您了,也不提醒爷一声;爷在她那待的这许久了,她是放一下都不肯么?!”
听得尤雨烟更是难受,咳着令她别再乱说。
“我才没乱说,那人不正是像不能没了男人一般吗?奶奶您也太善了,人家一进门就爬到您头上去了!咱做奴才的被人说两句是常事,可别人看的还不是主子的脸子?那人的鼻子都朝天了,您还替她说好话!”
尤雨烟更是咳得说不出话来,只是不断地摆着手。春梅见状大急:“奶奶别急,是春梅说错话了!”她轻抚主子的背脊,又去取来痰盅。尤雨烟急咳了一阵,吐出一口痰来;仍觉不适,又猛咳几声吐出一口血红方止住了。她抹了抹嘴,无力地靠在床柱上。
春梅把痰盅就光处一看,吓得脸也青了。却不敢张声,先搁在一旁,倒水给尤雨烟漱了口,扶她躺下了。
夏儿推门进来了,轻问:“奶奶怎么了?”
春梅心中慌乱,随口道:“没的事。要人时偏见人,不叫便自个儿来凑乱,歇着吧!”
“哟,我的春梅姐姐,”夏儿恼了,低叫道,“我能不进来吗?你说你能侍候好奶奶的,现她却咳得满院子的人都能听到了,上面不知道怪罪下 我也挣不开!”
“你倒怕上面怪了,”春梅晦气道:“你大爷他是聋了,奶奶就是咳破了喉咙他也听不到!”
尤雨烟这下清醒了,急道:“春梅,休得乱讲!”
春梅一呶嘴,不再说话。
夏儿见两人僵着,也不好说话,就去倒痰盅里的痰。瞧着颜色不对,走近油灯一看时,赫然一块血红,惊问:“春梅姐姐,奶奶吐血了?!”
“没有,别乱嚷!”春梅喝道。
“这……”夏儿指指痰盅。
尤雨烟转过头:“是我吐血了?……”
“没有,没有。”春梅急道。
尤雨烟正欲说些什么,又咳起来。春梅急急帮她抚背,夏儿立马取了干净的痰盅来……三人乱了半夜,直到天吐鱼白,尤雨烟方睡去了。
次日府里传得沸沸扬扬,说是骆荟把尤雨烟给气吐血了。
“这骆奶奶中真够厉害,竟把出了名好脾气的尤奶奶给气了个吐血!”阿寺道。
“也不能说骆奶奶怎么了,倒是看不出尤奶奶的气量心胸这么窄!”阿姚道。
小杜闻言皱眉道:“也不知骆奶奶给了你个什么好处,你不过娶了她的丫环,却就整天向着她,把良心也泯了。”
“正是!”小林附和说道。
阿姚摇头道:“我说呀,这两位奶奶又不走在一起,按理说怎么也起不了冲突。她自个儿吐血了,能赖得上别人么?”
“话虽如此,”小杜又道,“但这骆奶奶自持生了儿子,整天搞得家里不得安宁不说,光是她有事没事儿拉着咱大爷半天就让尤奶奶过得够呛的。”
“骆奶奶进门又不是一天两天了,她也早就习惯了吧?”
众人沉默了片刻,小林说道:“据说,昨天夜里尤奶奶不适,春梅去请大爷往院里去,大爷没去。定是因这事说了几句难听的话,尤奶奶病中见请不着夫君回来难过不说,春梅却受了一脸的气,回来说了两句呕气话就 尤奶奶给气着了。”
“这春梅往日里怪伶俐的,怎的这般不分场面?”小杜道。
阿寺道:“或不是气受大了,怎就会不知 矩?”
“你们又非亲眼所见,说的倒跟似真的似的。”阿姚道,“说归说,可别让人给听去了,又说咱们造谣!”
“你们造谁的谣来着?!”忽地一人道。
这话把众人吓了一跳,回头看时,却是小铃。小铃急道:“你们倒有心思在这儿闲事造谣,倒把我给急坏了!”
“什么事儿?”众人忙问。
“那个伊莱在晒衣时昏倒了,我到处找不着人!”
“哦。”众人应了一声,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,问了几句就散去了。阿姚想那伊莱有些什么问题,让小铃有消息立马通知他一声,请阿寺先去看看,自己又名人请郎中,就回樱仫身边去了。
“恩”郎中帮伊莱把完脉,抚抚胡须方慢慢开口道:“这小丫头有了身 , 不宜太操劳。”
“什么?!”阿寺故作惊慌。她打发了郎中便唤来一帮女主子与众管事,在下人间里等着伊莱的醒来。
伊莱一睁眼见了这阵势就吓坏了,可怜兮兮地望着阿寺,希望她能告诉自己该怎么做。不料阿寺倒是第一个骂了起来:“你这贱丫头,我殊不知你这般淫荡!快说,是和哪个野男人苟合上,竟还不知羞耻地怀上了他的野种?!你这贱胚子!”
她那里说得出话来?只一个劲地流眼泪。
“你可快快说出来!”
“没想到你这么坑肮,好个下流的胚子!”
“真是玷污了左家的名声!”众人也愤愤怒骂起来。
沈嘉鹤和洪落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,尴尬的不知所措,但这种破口大骂的阵势她们是做不出来的,只得在一旁看着。骆荟与尤雨烟抱病闺中自不露面。要数夏紫荆骂得最凶,这事儿不管,她能管什么?
“我对不起左家,我再无眼脸活了!”伊莱被说得受不住了,翻身就往墙上撞去。
这下可急坏了阿寺,吓坏了众人。正当众人惊得屏住呼吸的瞬间,青影一闪,却是阿姚拉住了伊莱,只听得樱仫在门口冷冷道:“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”
大伙一楞,都没反映过来。
“我会收她作小妾,不劳你们费心!”他说完就领着阿姚走了,留下一脸茫然的女眷和刚到的两位哥哥。
骆荟虽称病待在房中,可外面的事全别想逃过她眼里。樱仫娶不娶妾她倒不关心,可怎能让人在她背后说三道四的?心想:好,你要面子,我给!她本来就精神不佳,化了淡妆更显虚弱,领着小丽、小荷就往尤雨烟屋里去。
春梅见她来了,忙进房中替主子梳洗。才起身,骆荟就进来了,见了她便快步走上前去扶,口中道:“闻姐姐不适,多次欲要探望,无奈琐事甚多,难以分身……今闻姐姐血虚,都怪妹妹不好!本应好好侍侯姐姐,却把姐姐给气了……”说着,便拭去眼角的泪水。
春梅冷冷地立于一旁,不去劝解,亦不名夏儿奉茶。
小丽知她有意怠慢,却不发作。只细细劝道:“奶奶您亦劳累,且别伤心,想来尤奶奶心里明白,定然不会怪您。”
“姐姐大量不恼我,我还恼自己呢!”骆荟哭道。
“妹妹莫悲,姐姐怎会恼你呢?”尤雨烟柔声道,“我身子不好,家中巨细还劳你多费心, 又得顾着胜玑儿,把你累的够呛的了。”
“姐姐这话重了,我可担当不起!”骆荟又道,“昨夜里本要来的,不想咳得厉害,爷放心不下就搁了。却不知哪个短命的在姐姐跟前乱说,把您给气急了!我二人感情好,怎能让人造舌了去?”
尤雨烟欲开口,却猛一阵咳嗽,把话卡在喉间。
骆荟见状,道:“想来姐姐定是恼了我了!”说着就掏手帕去抹眼泪,“我知我进门这许久未曾侍过姐姐,姐姐是心里不怪让哪个说了也是会恼的。只怨这府中没有一个好的 子,都想咱们做主子的不和才好!姐姐心里虽明白,但我二人毕竟隔了一道墙,竟不知被哪个没心肝的蒙了姐姐的眼!我今日是掏了心要给姐姐看了,定不让那些小人得意。小丽,倒茶来,我要给姐姐认错。”
“是”小丽忙去倒了杯茶递到主子手里。
尤雨烟忙道:“这怎使得?妹妹快别这样。”
“姐姐喝了这茶,就是相信我了;若不喝,就是心里还有气,还恼着我!”骆荟双手捧着茶道。
“不,不……”尤雨烟急急摇头。
“姐姐果真如此气恼,我便长跪不起,直至姐姐气消罢了!”骆荟咽哽着,真个跪了下来。
“妹妹真真折煞我了!”尤雨烟忙去扶骆荟,动得急了,头上一阵晕阕,差点儿立不住脚。
春梅赶忙扶住尤雨烟,把她按下床来:“奶奶莫急,别把身子给急坏了。”再看一眼骆荟,心中好得意:你再嚣张,今个儿也得给我主子下跪!说道,“您该好好躺着才是,没的起来着了风!”
尤雨烟一听,想春梅怎地就不知大体?气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“你……”小荷刚想开口,却被骆荟一个眼神制止住了。
骆荟垂泪道:“我怎地这般无用?素日碍着姐姐的眼也罢了,今姐姐稍有不适,本是来探望却又让您着了风!唉,我真是个无用之人!”
“奶奶您是请罪来的,千般不该在尤奶奶处落泪。”小丽在旁道,“莫把尤奶奶处弄脏了!多少泪水都该往肚子里吞才是。”
“你说的是。”骆荟赶紧擦干了累。
小丽又道:“看这茶也凉了,尤奶奶越发不肯喝,待我换上一杯热茶来。”说着就接过那茶换。
尤雨烟刚顺过气来,眼泪 地急唤:“你们别忙了,好妹妹,好姑娘,我越发你们得罪了!看我造的孽!你再不起来,佛祖也会怪罪我了!”
“姐姐说啥也把这茶喝了,我就安心了。”
尤雨烟挣扎着扶起骆荟,只得把茶喝了,两人坐在床上说了许多体已话,骆荟方领着小丽、小荷离去。
- 06-09· 江西婺源成为中国茶叶出
- 06-09· 山东潍坊年底炒茶风又起
- 06-08· 【43】茗山生态茶
- 06-08· 怀念茗山长老
- 06-08· 我的慈悲主义--茗山法师
- 06-08· 大冶茗山猪场沼气土建工
- 06-08· 茗山中学简介
- 06-08· 以书传佛的茗山法师---茗
- 06-08· 继承茗山法师的遗志
- 06-08· 摘录:茗山长老日记
- 06-08· 厦门、鼓浪屿、南靖土楼
- 06-08· 安徽出发厦门鼓浪屿集美
- 06-08· [转载]实力派培训师张顾怀
- 06-08· 2010年06月25日--27日厦门三
- 06-06· 网站真实性核验名单Part
- 06-06· 广东东莞将举办粤港澳餐
- 06-06· 【资讯】:宜兴紫砂壶价
- 06-05· 产芝大石瀑
- 06-05· 名片大小_将垂直改设为
- 06-05· 东茗乡白岩村文化中心钢